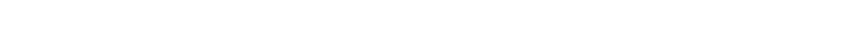作者:郎宏楠 顾楠
非自杀性自伤行为指在没有自杀意念的情况下采取的一系列反复、故意、直接伤害自己身体的行为。虽然施行者没有自杀意念,但因这类行为有可能导致死亡,因此是青少年死亡的主要原因之一。
青少年为何自伤?
非自杀性自伤行为在青少年群体中的发生率高于其他年龄段,那么,青少年为何选择自伤呢?心理学家认为,并非所有自伤行为都出于自我毁灭的动机,它们也可能出于自我探寻的意愿。
美国著名发展心理学家埃里克森认为,人的一生发展会经历八个阶段:口唇期、肛门期、性器期、潜伏期、青春期、青年期、成年期和老年期。在每个阶段,人都会经历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即危机。人在青春期(12-20岁)需要解决同一性危机(identity crisis)。如果青少年能在该阶段逐渐形成人生观与价值观、确立职业理想、了解自我,就能顺利解决危机,实现同一性整合(identity synthesis),反之,则将处于同一性混乱(identity confusion)的状态,难以作出坚定的人生抉择。埃里克森将极端的同一性混乱称为同一性迷失(identitydiffusion),同一性迷失的个体处于分崩离析的状态,感到极度空虚、难以体验幸福感。
同一性迷失给人带来两大负面影响:自我感的丧失与强烈的情绪困扰。丧失自我感者由于不知如何通过内在线索定义自我(如“我是一个善良的人”),只能通过外在线索定义自我。个别丧失自我感的人甚至会用自残行为来进行自我定义(如“我是一个自残者”),通过肉眼可见的伤痕,他们暂时了解了自己。而遭遇情绪困扰的人则有可能通过自我伤害以缓解情绪困扰。
埃里克森认为,任何一种身份若要得以维持,需要社会成员认同该身份的价值。然而,自伤行为不可能得到社会认同,因此非自杀性自伤行为绝非定义自我的长久之策。
在埃里克森之后,玛西亚提出,青少年对自我的追求可以分为探索和投入。探索指尝试各种选择,投入指对一系列价值观或人生决策的认同。根据探索与投入程度,玛西亚划分出四种同一性状态:同一性实现(高探索-高投入)、同一性早闭(低探索-高投入)、同一性停滞(高探索-低投入)、同一性迷失(低探索-低投入)。
研究发现,同一性停滞的个体更有可能作出非自杀性自伤行为,而同一性实现者最不可能自伤。
除了自我探寻,也有青少年通过自伤来管理情绪、惩罚自我、表达自我(如“我想通过自伤告诉别人我到底有多痛苦”)、对他人施加影响(如“我想利用自伤行为迫使别人做我想让他们做的事”)、惩罚他人(如“我想通过自伤行为让别人愤怒或羞愧”)。
如何预防和干预青少年自伤?
预防青少年自伤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我们可以将预防的重点放在青少年自我同一性的建立上。研究表明,父母的拒绝与控制都会影响个体同一性发展,让青少年失去探索与投入的勇气。因此,为了促进青少年自我同一性的整合,父母需要给予孩子足够的探索空间,并无条件支持青少年的选择,以好奇的眼光看待自己和孩子的想法、兴趣、价值观,比较双方的差异,思考哪些差异需要被尊重,哪些需要通过适当的方式加以指正。
对政府和学校而言,真正地落实素质教育可以给青少年提供更多自我探索的可能性。通过素质教育,青少年可能会意识到“相比数学,我更喜欢艺术”。此外,学校可以教学生通过冥想、倾诉等方式合理宣泄情绪,进行有效的情绪管理,并开设人际交往课程,让学生学习正确的人际交往方式。
在出现自伤行为后,必须采取及时有效的干预手段。无论是家长、老师还是朋友,一旦发现青少年产生了严重的自伤行为,请帮助他们寻求专业治疗,这不是什么难以启齿的事情,从同一性探索的角度来看,自伤行为表现了青少年强烈的自我探索欲望。
辩证行为疗法(dialectical behavior therapy)能较好干预青少年非自杀性自伤行为。该疗法并不一味强调要让青少年改变行为,而是对他们进行自我调节训练,帮助青少年接纳自己目前的状态,在此基础上进行技能训练,切实解决实际问题,即让青少年意识到“我现在已经很好了,我所做的一切是为了让自己变得更好”,拥有该想法后,改变自然会发生。
其实,作出非自杀性自伤行为的青少年很想好好活着,他们或因找不到出路而挣扎,或因达不到自己的期望而痛苦,或因有太多说不出口的话而在寻求帮助,所以,如果你看见了他们的“伤口”,请理解并帮助他们!
参考文献
Burke, T. A., Fox, K., Kautz, M. M., Rodriguez-Seijas, C., Bettis, A. H., & Alloy, L. B. (2021). Self-critical and self-punishment cognitions differentiate those with and without a history of nonsuicidal self-injury: An ecological momentary assessment study. Behavior Therapy, 52(3), 686-697.
Diana, C., Isabel, N., Cícero, R. P., Daniel, S. (2014). Risk trajectories of self-destructiveness in adolescence: Family core influences. Journal of Child and Family Studies, 23(7), 1172-1181.
Lear, M. K., & Pepper, C. M. (2016). Self-concept clarity and emotion dysregulation in nonsuicidal self-injury. Journal of Personality Disorders, 30(6), 813-827.
Luyckx, K., Schwartz, S. J., Berzonsky, M. D., Soenens, B., Vansteenkiste, M., Smits, I., & Goossens, L. (2008). Capturing ruminative exploration: Extending the four-dimensional model of identity formation in late adolescence. Journal of Research in Personality, 42(1), 58-82.
Manente, C. J., & LaRue, R. H. (2017). Treatment of self‐injurious behavior using differential punishment of high rates of behavior (DPH). Behavioral Interventions, 32(3), 262-271.
Michikyan, M. (2020). Linking online self‐presentation to identity coherence, identity confusion, and social anxiety in emerging adulthood. British Journal of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38(4), 543-565.
Miller, M., Redley, M., & Wilkinson, P. O. (2021). A qualitative study of understanding reasons for self-harm in adolescent girl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Research and Public Health, 18(7), 3361.
Ritchie, R. A., Meca, A., Madrazo, V. L., Schwartz, S. J., Hardy, S. A., Zamboanga, B. L., Weisskirch, R. S., Kim, S. Y., Whitbourne, S. K., Ham, L. S., & Lee, R. M. (2013). Identity dimensions and related processes in emerging adulthood: Helpful or harmful? Identity in emerging adulthood. Journal of Clinical Psychology, 69(4), 415-432.
来源|澎湃号·湃客“懂点心理学”